柬埔寨暹粒,是《古墓丽影》《花样年华》的取景地。如果你以为那里只是文艺腔调,那就太偏颇了。那里有文艺不能承受之深重,足够吞下你的故事、回忆和酒。

柬埔寨的石窟带有与生俱来的神秘色彩 三乐 摄
吴哥城、崩密列:废墟之上,万物重生
小吴哥就是吴哥寺,人们通常所说的吴哥窟,与长城、金字塔、波罗浮屠并称东方四大奇观。大吴哥指吴哥城,真腊王朝都城,距今千余年历史。

吴哥窟 三乐 摄
小吴哥并不在大吴哥城中,而是位于城外西北,约十分钟车程,有独立的护城河、城门。它不仅是寺,也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这里有世界最大的寺庙建筑群,密布在热带雨林中,体现了印度教和佛教信仰的艺术极致。建筑、砖雕、石雕,这里所有艺术形式都在神权合一基础上建起。高棉每个国王登基之初都会修建自己的寺庙,作为死去之后的陵寝,既是祭拜自己,也是祭拜神明。

吴哥窟 三乐 摄

吴哥国家博物馆
吴哥之行结束后,恰巧读到蒋勋先生的《吴哥之美》。这位美学大师,前后14次游历吴哥。

“吴哥的微笑”石雕群 Ayoway 摄
一座辉煌的王城,因战争和病疫被无情吞噬,在丛林中湮没成为废墟。那些夕阳下的断壁颓垣,仍雄浑而精细,隔着繁华兴落的尘烟,看见千年之前蒸腾的王者之气。

吴哥窟的幽深回廊
蒋勋先生写:吴哥的雕塑精细繁复,像织绣或印花,像一种迷离的光影。帝国会消逝,繁华也时时在幻灭之中。这些美丽的事物,与王朝的哀荣,所幸在文字影像间得以留存。

姐妹庙

高棉的微笑,是吴哥城巴戎寺中49座巨大的四面佛雕像,也有一说是54座。每一尊,无论斑驳程度如何,都是善良安详的会心微笑。这里的石头像有一缕魂魄,静下来,似乎能碰触到石头的呼吸、脉动、体温。
据说,这些是巴戎寺建造者阇耶跋摩七世的容颜。经历了战乱和鲜血,人性善意被权欲横加强暴,王城被侵略者攻占屠戮,文明覆灭死寂之后重生,这些斑驳的微笑依然如故。
蒋勋说,这些微笑像一部金刚经。因为微笑,文明不会消失。


同样深重的静默和震撼,在四十公里之外的崩密列。人的语言和文字总是囿于困局,越想描述触动心灵的事物,越是匮乏词穷。你无法用精准的词语去描述四面八方大片的废墟,倾颓的墙体和瓦砾,从那种颓丧、哀凉到极致之中,升腾起来的一种神秘光辉。

崩密列

崩密列
除了人与神灵,这里的动物和植物,也神秘幽暗。
苔绿色蜥蜴在断壁颓垣间蛰伏刺探;壁虎在雨后的餐厅外墙密集群居;阴狠的狼蛛在丝网上静候飞虫投降;猴子像侠士在密林间跳跃隐逸。山脚下夜市摊群旁,亚洲象驮着主人缓缓笃定地走来,像战功赫赫的老迈将军。

塔普伦寺

塔普伦寺的古树 Ayoway 摄
安吉莉娜·朱莉曾穿梭其间的塔普伦寺内,巨大的空心树水蛭一样牢牢吸附在寺庙间,纠结如一对对男女相爱相杀的虐恋。另有不知名的大树,根系盘错交织像蛇妖的长发,绵延数十米,深植在岩石间,发狠探寻着地底深处的秘密。
6号公路,浮世尽头叫远方
柬埔寨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美刀,当地货币瑞尔反而不受待见,景区内许多商贩不收。瑞尔实在不值钱,一般给酒店服务生的小费是2000瑞尔,兑换成人民币是4元。一碗面1万瑞尔,约合20元人民币,味道平平。“我今天吃了碗1万块的面条”成了游客们的一个梗。商品卖给中国游客实在不便宜,最普通的矿泉水也要1美元一瓶。

卖旅游纪念品的柬埔寨女孩 洁跳跳 摄

卖旅游纪念品的柬埔寨女孩 阿尔卑斯斯 摄
景区内外,随处可见守株待兔的小女孩。她们用生涩的中文喊哥哥、姐姐,一边说“姐姐你好漂亮”,一边用灰鸽子一样瘦小的身体横档在游客面前,兜售旅游小商品。有一回,我口袋里没有瑞尔,随手掏出一枚硬币递给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临上大巴前回头一看,她正愤怒地将硬币摔在地上,并踩上两脚。
贫穷、磨难和扭曲,是女孩最不应该承受的不幸。
一行人回酒店、赴景区、逛免税店,数次经过6号公路,它是暹粒最主要的一条道路。
用国内标准来看,6号公路并不宽阔,大约只相当于普通二线城市次主干道的宽度和风貌。两侧建筑普遍不高,因为吴哥窟高度约等于五层楼,官方规定,吴哥窟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周边建筑不得超过它的高度。
这是一条低调而奢华的街道。低调体现于触目之所见:平实,安静,除了早晚高峰,没有拥挤的车流与人群。奢华体现于它独特的交通地位:一边通往首都金边,一边通往柬泰边界。

彩虹桥上的神佛雕像 陈强 摄

彩虹桥上的神佛雕像 陈强 摄
最肆意的快乐,盛开在尘埃里
大榕树村,是总理洪森为了让外国游客了解柬埔寨居民的生活而创设的乡村体验景点。
大榕树村的女导游三十多岁,腕上佩着一串银镯,环佩铮然有声。在肤色黧黑、线条瘦削的东南亚人中,她是少有的肌肤微丰,眉眼含笑。将我们领进她家的二层木楼,临上楼前软语告诫,楼上有佛堂,不可拍照。
在茅屋颓垣随处可见的暹粒乡村,可以判断,她家是有钱人。陈设简朴整洁,近似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南方家庭。她的大姐,一名苍老谦恭的妇人,为二十多名来客一一让座递水。水是井水,清澈冰凉,盛装圆玻璃杯里,托盘呈上,有着一份尊重和考究。
将客人安置在一排排条凳上坐好,女导游不急不徐,像江南茶馆里说书的女先生,开始讲述大榕树村的风物。
她教游客用银梳刮痧,根据紫红色痧印的深浅疏密判断健康状况。她教游客用玉米须、芹菜、茄子蒂泡水,治疗三高。虽然这些知识都是为推销银器而铺垫,但并不惹人反感。
她说她的家乡不限制生育,村中最多的人家有16个小孩,她家算少,姐弟仅8个。
女人们生小孩不在家里,而是去神庙,在灰堆上分娩,她们相信神佛会保佑母子平安。新生婴儿用沁凉的井水濯洗身体,长大一些后并不圈养,任由在村中玩耍飞奔。生活虽然粗砺,儿童的餐具却必须用银碗银筷,她们坚信银质餐具可以消解食物的不洁。
这里的女人和儿童,似乎都身处矛盾的生存状态——她们命若草芥,在旱季四五十度的酷热中,在荒芜、恍惚的土地上,每年都有孩子夭折,每天都有产妇躺在破损的庙宇内,横卧在狼藉的草木灰上分娩,那种惊心,让我联想起萧红的《呼兰河传》与《生死场》。

路边小店的幼猫
生与死,这两桩人世间最大的事,在这里都仿佛不被重视。她们认真享受当下,在雨季来临时欢欣庆祝,女人们劳作之余用精致银饰明晃晃地装饰腰、颈、腕,半裸甚至全裸的孩子在村庄里追逐、骑车、尖叫,在炽烈阳光下,生命力肆意张扬。战争中被地雷致残的幸存者组建路边乐队,盲掉的眼睛和截肢的身体,都阻碍不了他们高亢快乐的歌声。

大榕树村的孩子 洁跳跳 摄
相比我们心心念念的“小确幸”,他们在苦涩生活缝隙中对快乐的追逐,显得更加酣畅淋漓。
信天命,而不怨天命。这是一个在常年战乱中渡劫重生的民族,灵魂深处的知足。
史诗,歌者,涂胭脂的神像
柬埔寨信仰蛇神,随处可见七头蛇、九头蛇的图腾雕塑。


与蛇神相关,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经典故事“搅动乳海”,在吴哥窟的浮雕中一再重现。大吴哥城南门的石桥两侧,由数十座神像连缀而成的雕塑群也是描述这一故事。

日影西斜,河流汤汤,夕阳余晖给一座座神像镀了金身。我最喜欢其中一尊浅灰白色的神像,他似笑非笑,神情里有悲悯。盯着看了许久,冒着关机的危险,耗尽手机仅存的8%电量将他拍下。
搅动乳海,说的是一场神与魔的大战。长生不老甘露藏在须弥山下的乳海中,善神和恶神商定,以神蛇Naga的身体为杠杆,合力搅动乳海。乳海翻腾千年,终于干涸露出甘露。随后善神与恶神为争夺甘露掀起世纪大战,大神毗湿奴用海水幻化成美女,引走恶神。正当善神们享用甘露时,有个恶神假扮成善神混入其中,也喝了一口甘露,甘露还在口中,尚未下肚,被太阳神和月亮神发现。毗湿奴立即射出法轮,砍下恶神头颅。恶神的身体死去,喝了一口甘露的头却得以永生。这颗头颅对日神和月神恨之入骨,无休无止追逐日月,偶尔把他们吞下,但喉咙已断,被吞进的太阳和月亮还是会跑出来。这就是柬埔寨神话中日蚀和月蚀的由来。

盲人乐队 朱军 摄
在暹粒最后一晚的《吴哥微笑》演出中,这一幕神话又由一位盲人音乐家演唱。木琴、铜鼓、单弦琴、三弦琴,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古老乐器交错弹奏,古老的高棉语如同无人破解的神咒,裹着风烟万里,从悠远的史诗中穿越而来,听得人从骨头缝里渗出寒凛。
血肉之躯,酷热之下漫长坚忍的劳役,垒就一片巨石之城的文明。我对高棉历史连一知半解都算不上,唯有惊叹旧时人们信仰的力量。

这尊佛像不知何故涂了红色胭脂
还有无数记忆片段,在匆匆忙忙的几天内,白鸟羽毛般轻浅掠过。是巴戎寺吧,不记得了,有一座奇异神像,脸和唇都涂了胭脂红,化了彩妆一样。在周遭的庄严中,显得莫名喜感,又匪夷所思。
这里太悠远神秘,其中细节故事,外人不能懂。只有脚下绵延的断壁颓垣,以及文明的吉光片羽,在记忆深处闪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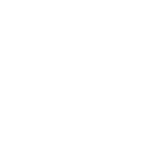
 2023年工业经济联合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五
2023年工业经济联合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五 安徽网库讯:兵团战友进江汽厂50周年纪
安徽网库讯:兵团战友进江汽厂50周年纪 安徽网库讯:庐江县郭河镇举行“金秋助
安徽网库讯:庐江县郭河镇举行“金秋助 安徽网库讯:线上发布安徽省企业社会责
安徽网库讯:线上发布安徽省企业社会责 安徽网库讯:热烈庆祝2020年全省工业行
安徽网库讯:热烈庆祝2020年全省工业行 安徽网库讯:衡山镇召开凤凰城建材市场
安徽网库讯:衡山镇召开凤凰城建材市场 安徽网库讯:“千村百镇唱大戏”走进金
安徽网库讯:“千村百镇唱大戏”走进金 安徽网库讯:庐江:满地“黄金甲”脱贫
安徽网库讯:庐江:满地“黄金甲”脱贫 安徽网库讯:长三角地区首届中国工业大
安徽网库讯:长三角地区首届中国工业大
 青岛一“钉子户”房屋四周被挖空成“孤
青岛一“钉子户”房屋四周被挖空成“孤 高清:湖南男子带3岁儿子冬泳 河水冰冷
高清:湖南男子带3岁儿子冬泳 河水冰冷 中国富商携儿子乘飞机视察法国葡萄园时
中国富商携儿子乘飞机视察法国葡萄园时 澳洲洋女婿迎娶西安姑娘 女方娃堵门要红
澳洲洋女婿迎娶西安姑娘 女方娃堵门要红 “私人定制”风靡深圳富人圈
“私人定制”风靡深圳富人圈 组图:济南放生两千斤鲤鱼遭“疯狂”捕
组图:济南放生两千斤鲤鱼遭“疯狂”捕 安徽网库讯:皖能铜陵公司青年突击队抗
安徽网库讯:皖能铜陵公司青年突击队抗 安徽网库讯:何树山副省长到皖能马鞍山
安徽网库讯:何树山副省长到皖能马鞍山 黄山秋色醉游人
黄山秋色醉游人 威马汽车陷退订风波 产品退订率高达三成
威马汽车陷退订风波 产品退订率高达三成 庐江县郭河镇:教育扶贫政策宣讲温暖了
庐江县郭河镇:教育扶贫政策宣讲温暖了 庐江县郭河镇举办“六一”儿童节文艺汇
庐江县郭河镇举办“六一”儿童节文艺汇